编者按 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李明教授在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4期发表题为“国家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路径研究”的文章。以下是文章内容。 [摘要] 生物安全已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是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关键。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目前生物安全内涵、生物安全事件状况及特点、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关键词:生物安全事件;生物安全治理;应急体系;应急能力;现代化 在2020年2月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疫情防控提升到生物安全、国家安全高度,指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1]我们认为,建设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推进国家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一、对生物安全事件及其新发展的认识 人类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生产、提供服务,也带来了风险问题,并成为政府政策困境,这是当代风险社会科技发展的显著特征。[2]生物安全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将酿成生物安全事件,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并对政府治理形成巨大挑战。 (一)生物安全事件内涵及演化的当代特征 生物安全事件是指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危险病原物质,以及现代生物技术所带来的生物危害或污染后果的事件。生物安全类事件中,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入侵、再发传染病、生物武器等类型事件,属于传统领域的安全事件;新发传染病、生物新技术误用滥用谬用、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流失、细菌耐药性(超级菌)、生物恐怖主义等类型事件,属于非传统领域安全事件。 人类应对传统安全领域的生物安全突发事件,与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同样久远。我国应对各类灾害的荒政史料中,有丰富的瘟疫类事件记载。从秦代(公元前221年)到清代(1911年)的2132年间,全国范围内的瘟疫事件达254次。[3]世界范围看,瘟疫一直困扰人类社会,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西班牙流感都让人类社会付出了惨痛代价。但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安全概念,是伴随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产生的。1976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制定的《关于重组DNA分子的研究准则》,是全球首部生物技术研究安全规定,首次提出生物安全概念。[4] 当代英文的生物安全概念有biosafety与biosecurity两个词,也有人分别翻译为生物安全、生物防护。前者是指防止非故意行为引发的危害事件的行为,如防控自然界中的人从动物宿主自然获得的感染,引发传染病事件的行为。后者指对主观意识支配下的盗窃、滥用等生物安全事件,采取主动防范措施,防止事件危害后果的行为。如实验室病原微生物实验中,发生的病原体泄漏事件等。[5] 近年来,相对于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领域的生物安全事件危害作用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新发传染病几乎每年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感染流行,生物新技术的误用、滥用和谬用事件也在挑战人类现有伦理准则,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流失事件则不断侵蚀国家主权边界。同时,相对于自然流行发生的生物安全事件,存在主观意识介入的事件更引发关注。自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及紧随其后的炭疽病毒粉末邮件事件后,包含更多人类有意识行为的biosecurity一词的应用范围更广,也表明了人们对待生物安全事件的倾向。 (二)当前生物安全类事件威胁类型 1.传染性疾病流行事件。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间、动物间或人与动物间传播疫情的生物安全事件,包括新发、再发传染病等事件。新发传染病是指30年内被发现的新种或新型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再发传染病指发病率显著减少后,再增加或流行范围扩大的传染病。[6]2003年SARS、2016年寨卡、2019年新冠肺炎等属于新发传染病。新发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复杂,有病毒、细菌、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及寄生虫等,人类缺乏认识,又无天然免疫力,健康危害大,社会经济损失严重。 2.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实验室病原微生物感染性材料在操作、运送、储存等活动中,因违反操作规程或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丢失等原因,造成的人员感染或暴露、感染材料扩散的事件。历史上先后发生过1967年马尔堡病毒感染泄漏事件,2005年H2N2流感病毒样本事件等。人们在反思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时认为,实验室硬件环境缺陷、管理不到位、人员操作不规范等是三个主要起因;损失扩大则主要是缺乏及时有效的应急处置措施导致。[7] 3.新技术谬用类事件。生物技术是典型的两用性技术,以基因编辑工具为代表的当代生物新技术发展,使恶意和违反伦理误用、滥用和谬用新技术的活动变得更加可能,成为新的事件暴发隐患,并带来灾难性后果。[8]如,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是典型案例。生物新技术误用、滥用和谬用仍属技术不当使用,最终挑战现存规则规范,与生物恐怖主义事件直接追求犯罪后果不同。 4.重大生物入侵事件。生物入侵事件主要是指某种动植物从外地自然、人为传入,或被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危害本地生态系统的事件。[9]如,美国亚洲鲤鱼事件、水葫芦入侵南方事件、1995年天津的美国白蛾事件等。生物入侵事件的发生,往往是被引入地生态对入侵动植物缺乏抑制功能,不仅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还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除了上述几类比较常见的生物安全事件外,还有生物恐怖主义、生物武器、生物资源流失、人类遗传资源流失、抗生素细菌耐药性(超级菌)等类型事件,虽然发生概率高低不同,但同样也对我国生物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三)当前生物安全事件的特点分析 一是系统性。生物安全风险发生、演变直至发展为事件,往往是由于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通过系列传导放大机制,带来整个系统的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无论是以微生物病原体感染为特征的新发再发传染病事件、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还是生物恐怖主义、生物入侵等事件,除了通过生物体作用产生直接影响外,都会扩展到整个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系统,形成长久、持续和破坏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 二是复杂性。从概率、损失矩阵分析角度,生物安全事件既包括概率低、损失大的“黑天鹅”事件,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事件;也包括较常见、损失大的“灰犀牛”事件,如各国经常性的流感事件等。从引发因素角度,包括自然因素导致的传染病事件;也有有意介入引发的事件,如生物恐怖主义事件等。从认知程度角度,包括对致病因子有充分认知的事件,如再发的血吸虫病;也有对致病因子认知不足的事件,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事件、世卫组织预测的X病毒事件等。 三是损害后果的全面性。生物安全事件不仅会对人类生命健康、动植物生存带来威胁,还通过影响劳动力、生产和社会秩序,深入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成为一种全面性的巨大危机。如,2003年SARS事件、2019年新冠病毒事件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2018年我国的非洲猪瘟疫情,引发猪肉市场巨大波动,对以猪肉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我国居民食品消费带来巨大影响。 四是危机的长期性、反复性。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类事件不同,生物安全类事件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传染病致病病原体可通过变异,衍生出二代、三代甚至更多,而且很多具有潜伏期,会与人类共生存,反复形成影响。生物入侵类事件更具有持续性、长期性甚至永久性破坏。如,1901年作为观赏植物引进的水葫芦,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猪饲料大规模引入后,自我繁殖扩张至今,已在很多地方形成生态灾难。 五是专业性、技术性特征。生物安全事件中,有的如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生物新技术误用滥用谬用事件,本身是技术和专业研发过程的产物;其他的如传染病事件、生物资源事件应急管理,也需要深度的专业技术参与。同时,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进入生物领域,未来生物技术也带来网络生物安全隐患。这一特点决定生物安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设计,不同于其他领域,这是各国采用专业部门管理模式的重要原因。 二、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 面对当前生物安全领域事件频发带来的巨大挑战,只有通过加强生物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才能有效处置应对,为技术发展保驾护航,从根本上保护人民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 生物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是一种全面性、综合性和规范性制度安排,由生物安全应急管理主体、客体和运行关系三要素构成。它既包括体制、机制和法制等静态制度,也包括了执行、遵从和运行的动态应急管理行动。第一,主体是应急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外在表现为体制,即组织形式及职能分工,也包括对职能履行行为。如农业农村部、卫健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承担动物防疫、卫生防疫、生物技术伦理、生态安全等事件的应急管理职能。主体也包括事件涉及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社会公众等。第二,客体是围绕各类事件的应急管理对象。如,甲型H1N1禽流感事件中的疫情,致病生物因子、病毒污染环境、病毒感染病员等,都属于生物安全应急管理的对象。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客体的外在表现为体制机制,即事件应急管理系统的组织、对象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第三,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关系是指主体、客体间关系及其运行过程。如,实验室生物安全应急管理中,政府对事件应急决策,政府对密切接触人的隔离,科研机构对受污染环境消杀,医疗机构对受感染人员的救治,主管部门对外界的信息发布等。这种关系常通过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预案等制度化形式表现。 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单位和管理者个体,通过防范和控制事件中的生物致害因子,减轻消除威胁的能力。生物安全应急能力通常适用预防原则、准备原则和先期处置原则,[10]核心目标是避免事件发生,主要包括监测、预警、鉴别、处置、恢复等方面的能力。[11]生物安全应急能力通过应急管理体系的主体、客体和关系等各要素发挥作用。一是应急主体能力的全面性。生物安全事件系统性风险特征,需要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纵向、横向上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应急职能协调、资源配置能力。二是应急客体能力的激励有效性。通过应急管理各环节机制的有效设计,实现应急管理各环节的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处置应对、恢复重建的能力。三是应急管理关系的规范能力。规范能力通过增强应急管理关系的确定性,实现应急管理参与者行动的可预期性,进而对冲应急事件的不确定性。 (二)我国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进展 在2003年SARS事件暴发前,中国在传染病防控和病原微生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生物安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2003年SARS事件中,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恐怖效应强的SARS病毒疫情,凸显了我国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危机,当年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使得生物安全概念进入政府管理视野。SARS事件后,我国开始了全面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2005年制定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制定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四大类突发事件,并初步建立了“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制度体系框架。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后,围绕各类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应急响应、应急处置、恢复重建等环节,全面开始了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在国家总体的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过程中,先后明确了卫健委(原卫生部、原卫计委)、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等部门的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职能。我国也先后围绕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动物疫情、实验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普遍开展了生物安全法律法规规范建设,并制定了一系列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应急预案。如,国务院颁布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根据传染性、危害程度指标,将病原微生物分为四类。原农业部、原卫生部颁布了《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和《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开始全面加强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工作。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加强,我国已建成2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50多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用于第一、第二类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研究工作。2004年建设了全球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也为疫情监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职能整合弱化。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职能多部门承担是现代分工的常态,但应同时具备整合能力。目前基本上处于条块分割状态,基本的信息共享难度大,缺乏统一行动,存在各自为政的弊端。 生物安全事件发生、发展、演化和危害后果等各环节具有系统性,致害生物因子也往往跨越人和动物、不同区域间相互传播,这与职能分割、分散又缺乏整合的状况产生矛盾。通过联防联控、部际联席会议等机制,体制内各部门尚能实现有效协调,但其他主体参与呈现碎片化、分散化。从资源角度,财政投入之外的社保、保险等资源进入也较少,救治基础设施、设备储备不足,专用药品、器材的紧急生产能力不强。[13] 二是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制度建设滞后。制度不统一带来法律规定冲突,造成应急管理行为困境。如《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冲突,主要表现在对于预警信息发布的法律冲突上。同时,新兴和关键领域法律法规和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如缺乏统一的生物安全应急管理的法律规定,某些生物新技术领域,如生物识别技术法制落后于实践。[14]虽然即将出台的《生物安全法》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法律冲突和生物安全应急法制滞后问题,但专门法与一般法的冲突依然存在;同时,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应该主要对标生物安全法规还是应急管理方面的一般规定,依然是个现实问题。 三是应急技术装备、基础设施有待提高。我国生物安全应急管理核心技术、关键装备依赖进口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如呼吸机虽然装备数量多,但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常用防护用品,甚至口罩等应急产业存在规模小、做代工、技术含量不高等通病。作为生物安全应急管理技术支撑的实验条件和仪器设备亟待升级改造,为预警和应对生物安全事件奠定坚实基础。以一类、二类高致病性病原实验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为例,美国截止目前有15个四级实验室,1300个三级实验室,分别是我国的7倍和30倍。 四是对生物安全新领域事件追踪关注有待加强。如,随着生物信息越来越具有重大军事、经济和社会价值,生物信息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领域。但目前我国针对新兴生物安全领域的应急管理依然存在战略不清、政策不明、社会重视不足、技术不强等重大问题,为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生物安全事件埋下了隐患。 三、推进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路径 推进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应对生物安全事件的基础性解决路径。一般意义上的治理现代化的最典型特征是,社会分工细化及其相互协作的动力机制设计,具体包括体系的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等5个方面标准。[15]判断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是否实现现代化,主要视其是否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各领域,并实行分工细化和协作,协调增进应急规划、应急规范、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科技支撑5个方面能力,促进整个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协调高效发展。 (一)增强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规划能力 确定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规划价值理念、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方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视野。强调生物安全应急规划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推动生物安全政策嵌入到其他政策领域,推动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规划与其他应急管理规划的协同。促进生物安全突发事件的协同治理,纵向上划分政府间事权划分,横向上建立重要领域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协调机制下的分部门管理体制。超前规划一段时期内,应重点关注的生物安全事件类型,分析生物安全事件的形势。通过生物安全应急能力规划的实施,增强全社会的生物安全风险防御意识、风险应对能力、应急准备能力、响应机制和恢复重建等能力目标。 (二)增强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规范能力 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增强人类行动的预期性,防范不确定性。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规范化就是以法律法规、应急预案、标准规范等确定性的制度规范,去应对生物安全事件的不确定性。针对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体系、生物因子调查、名录清单管理、风险监测预警等不同领域,建立生物安全应急管理的标准体系。根据即将出台《生物安全法》,清理相关的制度规范,解决法律冲突,减少规范缺失,充实应急预案,完善技术标准,形成一套完整的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制度规范体系。 (三)增强生物安全事件预防预警能力 一方面增强日常的预防准备能力。增强生物安全风险意识、风险排查、应急预案、培训演练和物资储备等预防方面的能力。培育生物安全风险意识,是做好生物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心理基础;做好日常生物安全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是关口前移的重要内容;完善预案,做到一事一案,开展经常性演练,持续动态修订;研究完善储备目录,既应当包括药品、防护用品、医疗器械,也包括通用性生活物资储备。另一方面增强事前的监测预警能力。增强对生物安全风险的动态监测、风险感知、事件预警能力。其中,威胁的动态监测能力是起点,是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先进性体现。[16]要配置硬件设施设备和专业操作技术人员,提高针对应急对象的长期动态监测能力;要做好人机结合、人工与系统整合工作,增强风险感知能力;要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使应急管理者有激励进行初始信息披露和事件预警。 (四)增强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响应能力 生物安全事件大多属于波及面广的一类事件,涉及到全体社会公众,生物安全应急管理要深入到全体社会公众和机构。一方面要增强厂矿、企业、学校、社区应急能力建设,开展经常演练、疏散和集体培训学习。二是要推动交通、物流、物资供应等行业的应急响应能力,开展全面预案建设、重大情景构建、经常性演练。三是推动生物安全事件应对的军地、军民融合工作,通过加强信息化、完善预案、改进力量投送方式、追踪生物安全新领域、人员装备组合科学化和实战需求测算精确化等方面工作,加强军队防疫救援的组织管理、应急响应、远程投送、越野机动和自我保障等能力,提高军队应急防疫救援能力。 (五)增强生物安全应急科技支撑能力 均衡规划高等级实验室布局,及时收缩小、零、散的局面,增强重大科技设施的实用性。加大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鼓励和扶持自主研发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等途径对生物安全工作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等。组建专门生物安全政策战略研究智库机构,加强国家生物防御、反恐、生物入侵等生物安全研究及对策分析工作。发展生物安全产业,推动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关键和常用技术设备国产化,改变从口罩、呼吸机到防护服等基本防护用品、设备设施依赖进口的局面,推动中国生物安全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Fischer, Julie E. Bi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Policy Landscape. Stimson Center, 2004, pp. 11 24, Speaking Data to Powe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ealth Expertise in the National Biological Security Policy Process, www.jstor.org/stable/resrep10981.7. Accessed 23 Feb. 2020. [3]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0. [4]车静. 生物安全管理的基石:阿西洛马重组DNA会议研究[D].浙江大学,2016. [5]王子灿.Biosafety与Biosecurity:同一理论框架下的两个不同概念[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6]马雪征. 人类新发传染病和再发传染病:病毒类和寄生虫类传染病[J].国外科技新书评介,2016(10). [7]裴杰等.实验室生物安全发展现状分析[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9 (9). [8]郑涛. 生物安全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32. [9]王磊等. 全球生物安全发展报告(2017~2018年度). [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9:25. [10]Rosalyn Diprose, Niamh Stephenson, Catherine Mills, Kane Race and Gay Hawkins. Governing the Future: The Paradigm of Prudence in Political Technologies of Risk Management. Security Dialogue, Vol. 39, No. 2/3, Special Issue on Security, Technologies of Risk, and the Political (APRIL/JUNE 2008), pp. 267-288 [11]郑涛.我国生物安全学科建设与能力发展[J].军事医学,2011 (11). [12]郑涛等.以能力建设为中心,加快我国生物安全科技发展[J].军事医学, 2014 (2). [13]袁志明,刘铮,魏凤.关于加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建设的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 (6). [14]苗争鸣,尹西明,陈劲.美国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启示:以美国生物识别体系为例[J/OL].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15[2020-03-0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117.G3.20200222.1020.002.html. [15]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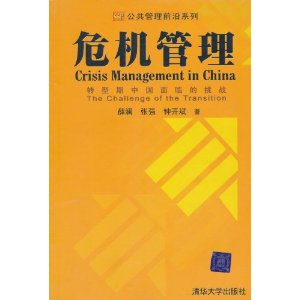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已有 0 条评论,查看更多评论»